当前位置:首页 > 九州图书 > 媒体九州
叶曙明:我是一个历史说书人
来源:贵州都市报 信息员: 更新时间:2015年06月02日

叶曙明:作家、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著有《山河国运》、《大变局:1911》、《国会现场》、《草莽中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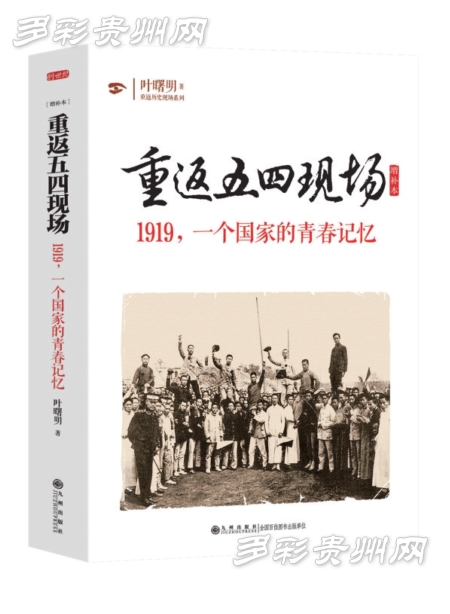
《重返五四现场》[增补版] 叶曙明著 九州出版社 2015年5月出版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史上群贤咸集,大师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像山崩川涌,汇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荡,引领风骚。那是一段激情迸发、令今人无限神往的光辉岁月。
六年前,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作家叶曙明推出《重返五四现场》一书,再现了这个新旧政治、新旧文化交锋的大时代,细述民国政界与学界的风云往事。为我们细腻而有条理地梳理呈现了民国史上重要的一个片断,它不但扩充了我们对民国史的了解,也为我们反观身处的时代提供了一个角度。他在书中将1895年的公车上书视为“五四”时代的起点,又将陈炯明评价为与梁启超、陈独秀并立的新文化运动三个代表性人物之一,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今年五月,增补版的《重返五四现场》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叶曙明在序言里谈到,“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是首次把知识分子的诉求引向对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但再版时,叶曙明直言他不再关心“五四”运动的起点,却更在意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五四”时代。
评论家、学者解玺璋说:“长久以来,‘五四’被各种思想搞得面目全非、奇形怪状。现在,我们跟随叶曙明,穿过重重迷雾,重返‘五四’现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五四’的真相。”
叶曙明早年以写小说著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叶曙明一度与莫言、余华、格非等当代著名作家齐名,他曾被文艺界称为“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1996年发表了小说《垃圾成山的日子》后,他觉得“文字已经没法表达出我内心的想法了,写出来的每句话都不是我想说的,我觉得再写下去就要疯了。”于是,在放弃写小说后,他走进历史,与历史对话,与古人对话。最初是为了逃避而进入,但进入以后,发觉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海洋,再也不想离开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叶曙明的《草莽中国》出版,首次从地域文化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引起读书界的巨大反响。之后相继出版《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国会现场:1911-1928》、《李鸿章传》、《山河国运: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等作品。
现在,叶曙明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历史说书人”。他觉得自己所写的,都是与历史人物对话的结果。在与历史的聊天中,他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无论是陈炯明、梁启超、孙中山,抑或是章太炎、陈独秀。“我也可以说‘我的朋友胡适之’、‘我的朋友陈竞公’了,只不过在他们的朋友里没有我叶曙明而已。”他说。
尽量还原“五四”人与事
文化周刊:关于“五四”,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人割断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也有人认为它开启了现代文明之路,您自己怎么去看这段历史?
叶曙明:“五四”是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由当时的各式人等共同创造的,因此,你从任何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都会看到不同的“五四”,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说它是启蒙运动,有人说它是爱国运动,有人说它是青年运动,有人说它是全民运动,有人说它是民主自由,有人说它是暴民政治。这是因为每个人看历史的角度不同,想达到的目的不同,所以各说各话,谁都没有误读,只是各取所需而已。《重返五四现场》,就是试图突破“五四”被符号化后的重重外包装,采取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谨严态度,来尽量还原五四时期人与事的生动场景。
文化周刊:您的书分为上篇“启蒙”,下篇“救亡”,这是概括“五四”运动的关键词吗?
叶曙明:“五四”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任何想用简单的几个概念把它归纳起来,都会有捉襟见肘、词不达意之感。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魅力所在。我用这两个词划分上下篇,不是要定义那段历史,而只是想传达一个意思:这是两个不同的“运动”,是历史的一个拐弯处。至于是把上篇命名为“新文化运动”,下篇命名为“五四运动”;或者上篇为“百家争鸣”,下篇为“二元革命”,均无不可。
文化周刊:您在书里将陈炯明,与梁启超、陈独秀一起列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旗手。为什么要重新定义陈炯明的地位?
叶曙明:因为我觉得他是真正理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他没有搞群众运动,没有演双簧戏,没有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没有主张全盘摧毁传统文化,他是真正一点一滴地把新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当时那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在广东禁烟、禁赌、办大学、办平民教育、推行城市清洁卫生、制订省宪法、维护言论自由、推行自治运动等。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书生小圈子里的笔墨官司。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面。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文化周刊:历数《重返五四现场》、《重返辛亥现场》、《国会现场》,您的几本书均名有“现场”二字,您怎么去理解现场?您是想尽可能地为读者还原历史现场吗?
叶曙明:我们现在仍在现场。只不过我们每个人进入现场的时间、位置不同而已,有些人第一幕就出场了,第二幕就挂掉了;有的人是第二幕、第三幕才出场……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乱时代,但大时代的风云,还是见过一些的,所以我知道,“剧情”并没有中断,冥冥之中的那个“导演”也没换人。我想告诉读者:别忘了你仍在现场。
历史的有趣之处多在细节,我只是把我从我这个角度看到的历史说说而已,希望在故事上能自圆其说,在逻辑上能说得通,就满意了。
文化周刊:您如何再现这本《重返五四现场》的历史现场?书中有大量的细节描写,感觉现场感十足,您是如何把握历史资料的?您原本是写小说的,这种对细节和现场的描述会不会有读者认为是在演绎历史?
叶曙明:我写历史,是以官方档案为骨架,以私人笔记为血肉。官方档案是指朝旨、奏章、会议记录、决议案、公函、文告等;私人笔记包括书札、日记、回忆录、报纸报道以及一些时人所写的野史杂记。我甄别史料的办法,基本就是靠海量的阅读,一直读到我对这个人像老朋友一样熟悉,对他的举止言行,已没有什么意外了,他会不会说这句话?会不会做这件事?他是怎么想的?动机是什么?我凭对他的了解就能判断。我承认这样取舍史料,会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但历史本身就是带感情色彩的。我的原则是我不捏造史料,不虚构情节,但我采信哪条史料,则是根据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作出的纯主观判断。如果有谁想改变我的看法,最好不要以史料的真伪来质疑我,因为你也无法证明你掌握的史料就是真的,你只能说:我还有别的史料,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呢。这样,我会非常乐意听,然后再作出我的主观判断。
在我的历史书中,我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也就是“五四”青年上街游行时,在马路上欢呼鼓掌,如同矮子看戏一般喝彩的人物。我所看到的,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我也不指望能够看到全部;我的理解肯定也是非常受个人学识、修为、表达能力的局限。
我爱好历史,但从不在意它的学术性,我在微博上把自己定位为“历史说书人”,因为我写的都是我与历史人物对话的结果。我没打算推翻什么,也没打算建构什么,一切都是与历史聊天而已。
跟着史料走是一种乐趣
文化周刊:现在有一股“民国热”,有一些人对民国充满了美好的向往,您怎么看民国?
叶曙明:说民国好,说民国不好,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这是因为民国政治、文化的血缘关系比较复杂,我简单梳理一下,至少有四大血亲:一是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儒家传统);二是沙俄,包括后来的苏俄;三是日本;四是欧美。赞美民国的,大抵是说它与中国传统或欧美有关的部分;批判民国的,则主要是说它与俄国、日本有关的部分。换言之,民国在大陆这短短的几十年里,好东西都是来自本身的传统与欧美,坏东西都是来自俄国与日本。事实是否如此?可以细细研究。我觉得这四大血亲,在民国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表现得有强有弱,不能一概而论,否则会有盲人摸象之虞。
文化周刊:可以说说您的历史观吗?
叶曙明:我没有什么史观的,就是跟着史料走,顺其自然,史料去到哪我就跟到哪。我也没经过任何正规的历史研究训练,就是积累史料,跟着史料走是一种乐趣,因为你不知它会把你带到哪里去,这个过程,有点像玩拼图,你手里有一大堆碎片,把它们慢慢拼出一幅完整的图来。至于这幅图最后呈现的是什么景象,我既不能决定,也无法预测。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64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64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