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九州图书 > 全部图书 > 大众阅读
历史的张力:重寻11位英雄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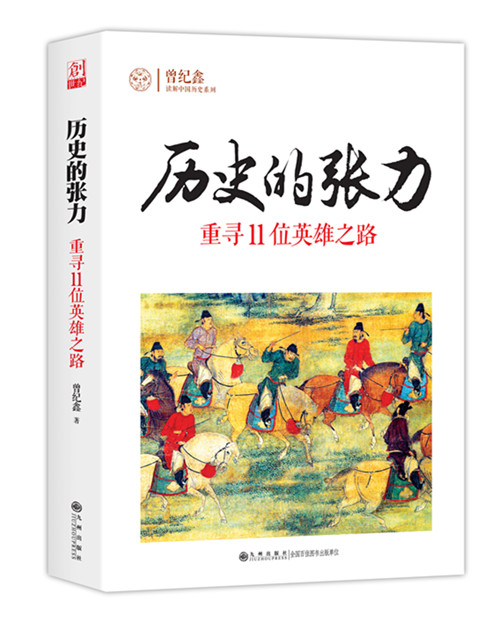
一、内容简介
本书叙写、读解的十一位历史人物,有被后世誉为“智绝”的诸葛亮,创作世界第一部茶书的陆羽,“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的朱熹,七下西洋的郑和,编撰《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面临时代巨变作出“另类抉择”的萨镇冰,不惜生命高风亮节的瞿秋白,还有“半截子英雄”李自成以及作者笔下少有的女性人物——肩负和亲使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他们都是当时的英杰,其成就往往就是一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山峰。
作者除大量阅读、考证外,还前往这些历史人物的故居、墓葬、纪念馆以及相关遗址,考究故迹,还原事实,揭示真相,感悟历史,以点带面,探寻价值,阐释意义……这种“历史的在场性”写作,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极富弹性与张力。
二、作者简介
曾纪鑫,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各类体裁作品数百篇,出版专著二十多部,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著作进入全国热书排行榜。其作品被报刊、图书广为选载、连载,部分作品入选面向21世纪课程《大学语文》教材,被全国媒体广泛关注、评论。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
代表作有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大明雄风:俞大猷传》等。
三、目录
王昭君:边塞秋风
面对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昭君深明大义,以其个性的丧失、个体的压抑为代价,弥平了华夏、匈奴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弥合了两个民族曾经有过的伤痕。
诸葛亮:走出古隆中
诸葛亮虽然走出了古隆中,但终其一生,也未能走出“隆中意识”,他自从走出隆中后便一次也没回过隆中。
文成公主:高原壮歌
能回而不回,思归而不归,文成公主的内心,便在这没有止境的思念与决绝、牵挂与抛舍的两极间,做着无以解脱的痛苦撕扯,直到三十年后身染恶疾,抱病而逝,被藏族人民尊为绿度母。
陆羽:茶韵仙骨
陆羽仿佛为茶而生,他的清贫生活、习儒诵经、东奔西走、辗转磨难、艰辛坷坎……一切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字:茶!
朱熹:理学的拓展与困境
朱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符号,更是一个由许许多多的侧面与层次,包括正面与背影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
郑和:七下西洋的悖论
大海虽然充满了风浪、颠簸与险恶,但也给了他权力、自信与荣光,他深切地感到,海洋才是他建功立业、自由挥洒的广阔天地。
李时珍:医中之圣
若从三十五岁那年挥毫写下“本草纲目”四个大字算起,这部医书,整整耗去了他二十七年时间。后半辈子光阴,二十七年心血,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个浸透纸背的密密麻麻的墨迹。
李自成:英雄的出路与末路
作为一个当初唯求生存的下岗驿卒,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各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林则徐:睁眼向洋看世界
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而痛苦的转变过程,由“通时务”变为“通夷务”,从严禁鸦片过渡为奖励通商,最后发展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萨镇冰:时代风云中的抉择
萨镇冰是一个拎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没有机心,视名利如敝履;他清心寡欲,鳏居了大半辈子;他生活简朴,不为自己与家人谋取私利……同时,他完全称得上一名具有血性与良知的军人。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
前面已是绝壁,路已尽,灯将灭,他无法再生,可在回望来路时,尽管“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与完美更是相距遥远,可他不觉得可惜,不觉得后悔。
四、编辑推荐
曾纪鑫“历史的在场性”写作成果
考究历史现场、相关遗址
还原事实,揭示真相
让人物复活,彰显弹性与张力
五、精彩书评
曾纪鑫是中国最早写作文化历史散文的作家之一,他是一位有现实关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他的文化历史散文偏重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现代认识与评价,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富有当代作家的人文情怀,是中国近年来散文写作最重要的收获。
——谢泳(著名学者,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显示出丰富的历史知识、开放的文化思想、敏锐的人文触角、纵横捭阖的叙述技巧以及流畅有力的语言风格,大视野、文化味和历史感构成了他的文化历史散文的独特性。
——林兴宅(著名文艺理论家,象征论文艺学倡导者)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风格刚健硬朗,是“学、行、思”的统一,是史笔、诗情与哲思的会通,达到了“人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是非同凡响的跨文体写作,是新千年中国文化历史散文的重要收获。
——李钧(著名文学评论家,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六、序言
历史的在场与弹性
历史已成过去,它就在那儿“呆着”。正如仓央嘉措《见与不见》所言:“你见,或者不见我 / 我就在那里 / 不悲不喜……”(一说作者为扎西拉姆·多多)只有后人介入其中,“死”去的历史才会“复活”。这种介入,即所谓“历史的在场”。于是,逝去的历史,由静止而运动,由客观而主观,由零度而深度……就这样以一种无可比拟的鲜活与生动,呈现在我们眼前,变得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与感情色彩——经验或教训,美好或丑陋,亲切或厌恶……
当然,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介入所呈现的弹性,虽然可伸可缩、可厚可薄、可宽可窄、可大可小、可多可少,但毕竟具有一定的限度,它所呈现的“空筐”并非无所不能、无所不装。能装哪些内容,可纳多少容量,完全受制于历史所提供的信息及其特性。当然,也与介入者活动的广度与深度密切相连,但决定因素仍在历史本身的“硬性”。
收入本书的十一篇文化历史散文,涉及十一位古代、近代、现代历史人物,虽创作于不同时期,但都是阅读与行走的收获,一种个体生命以其独特方式介入历史的产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从小的心愿、志趣与理想。三十多年来,所接触、阅读、研究的历史人物及走过的地方多矣,但能够出现在我笔下的,毕竟少之又少。这种选择取舍,既有机缘,也与个人性格、爱好、学识相关,更多的则取决于“在场”时刻对历史人物的内心触动与感受。记得《小说林》杂志刊登《边塞秋风》与《高原壮歌》之时,主编何凯旋兄曾两次嘱我写下创作感言,并配个人照片在封三发表,其中的一则如是写道:
去了一趟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觉得昭君和亲达致匈、汉之间的和解与和平,于国家、民族而言,功莫大焉;但对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由一柔弱女子承担仅凭军事、战争而无法达到的目的与效果,其艰难与悲苦可想而知。若从现代人的思维与视角,对昭君和亲这一史实的发展演变还其本来面目,对其个人性格、心理、命运,对相关遗迹的历史积淀等进行一番个性化的探究与描述,必能拓出一片新的创作天地。有感于此,遂成《边塞秋风》。
《边塞秋风》是这样,其他篇章也是如此。比如创作《高原壮歌》,自然得益于西藏之行,对那片离蓝天最近的、人类最后一块净土感慨多多,而触动最深的,还是文成公主。在山南藏王墓区松赞干布陵墓,墓顶有座古庙,里面供奉着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塑像。文成公主前往吐蕃和亲,十年后夫君松赞干布离她而去,此后又在西藏生活了三十年。其实,文成公主有三次归返长安的机会,为了唐蕃之间的和平大业,她都主动放弃了,逝后与松赞干布葬于一处,与藏地的大山融为一体。作为一名弱女子,这该需要多强的意志与决心,多大的勇气与担当呵!其所作所为,不正是一曲在天地间回荡了千百年之久的高原壮歌吗?
王昭君与文成公主,是我笔下众多历史人物中少有的两位女性,典型的巾帼英雄!
这些令我产生创作欲望的人物,都是当时的英杰,他们在某一领域、某些方面的成就,往往就是一座高峰。比如诸葛亮的“智绝”,在国人眼中,他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令人仰止;朱熹学说的“集大成”恢宏规模,朱子理学的博大精深、理性思辨,在古代中国无人匹及;陆羽创作的世界第一部茶书——《茶经》,涉及茶艺、茶道、茶事等方面,搭设了茶文化的基本构架,勾勒了茶文化的总体轮廓,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体系的正式形成;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一经问世,便成为中医学的一座“珠穆朗玛峰”;郑和七下西洋,无论是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还是航程之远、所达地方之多,在当时都堪称世界之最;而林则徐在千百年来的“天下观”及清代闭关锁国的背景下,通过禁烟运动,对西方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与了解,被后世史家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而,通过阅读与走读,我发现,正是这些人物身上,因时代、环境、文化、制度、心理、认识等方面的限制,皆有着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诸葛亮的“隆中情结”,决定了他的人生格局与成就大小;朱熹的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其他诸子学说,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郑和下西洋无论航行多远,只能是明王朝威恩并重、扬威海外的虚荣性满足,永远也进入不了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全球一体化时代;林则徐看到的西方不仅有限,而且有误,那种以“天朝”的盲目自信应对“英夷”的轻蔑不屑,以及实用主义的短视倾向,使得后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大打折扣,难以深入形成体系;李自成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代表,占领北京后无法转型,惨遭失败,中国古代的“半截子英雄”现象,在他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历史人物的作用与意义,不得不受制于这些无法克服的局限。对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历史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有限“张力”。
尽管如此,我在这些所描写的历史人物身上,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挣脱局限与束缚的努力。历史之河浩浩汤汤,个体生命浸入其中,渺小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人”字一撇一捺的相互支撑,构建了人的站立、不倒与伟大。引用一段雨果广为人知的名言:“比陆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可见人的胸怀、自由的心灵可以超越一切,这便是一种独特的至高无上的人格魅力。
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但是民间的口碑,千百年来的潜在价值观,并不以成败得失衡量某一历史人物,他们看重的,是人格、品性与风范。也正是这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史观,使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历经风雨、颠踬、挫折之后仍永葆活力,长盛不衰。
若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瞿秋白无疑是一位失败者,被敌方抓获、关押、杀害。然而,他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与豪杰,只要他愿意,一个“降”字,就能苟活于世,就能获得新的荣华富贵,可他选择了死亡,含笑而逝。死既死矣,不惜误解与责难,还要留下一部袒露心灵,展示真实灵魂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
人生在世,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定的难以避免的抉择之中,小至吃喝拉撒,大至道德信仰。不同人物的选择,其意义与影响大不相同。小人物的选择微不足道,大人物的抉择举足轻重,影响乃至改变历史。萨镇冰的地位并非显赫,名气也不是很大,但其一生,不得不面临多次重大抉择。这种抉择对历史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却有着一定的“示范”意义。他的选择在非此即彼的传统社会显得有点“另类”,那就是非敌非友,走第三条道路——放弃或逃避。这种选择,既非胆小怕事,也非患得患失,更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责任与担当。历史过于恢宏,萨镇冰所能做的,就是听凭正义与良心的召唤,不惜舍弃既得的权力与利益,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的一种抉择与境界,令人敬佩不已。
其实,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盲人”,对周边的情形、局势的发展、未来的走向并非清晰明了,哪怕那些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也不例外。唯有经过一定时段或一番积淀,后人打量观望,于当时难以超拔的历史情境,难以洞悉的历史谜团,难以把握的历史节点,才会豁然开朗。
对所选取的历史人物,我一般不会轻易动笔,也不会信口开河人云亦云,须搜求阅读与之相关的所有找得到的文字图片资料;对其故居、墓葬、纪念馆等,还得置身现场,考究原貌,还原真相;哪怕推理与想象,也得合乎情理,遵循一定的历史逻辑与规则;对其叙写,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有所侧重地就其人生的某一重要部分或我感兴趣的方面展开笔墨。
不停地阅读行走,不断地思索探寻,使得我常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这种切入历史的状态以及“在场性”的描述,不得不打上一定的时代烙印与个人色彩。这种“硬性”与“弹性”相互映衬的创作宿命,也决定了一个作者的价值取向与作品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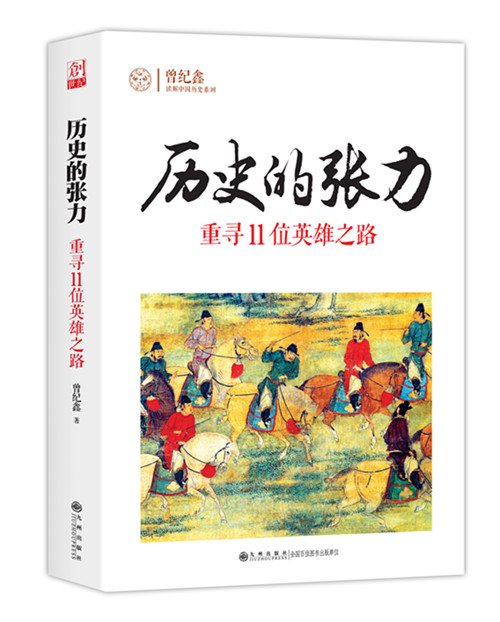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64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64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