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九州图书 > 最新动态
徐复观的峻厉与萧逸
来源: 信息员: 更新时间:2014年11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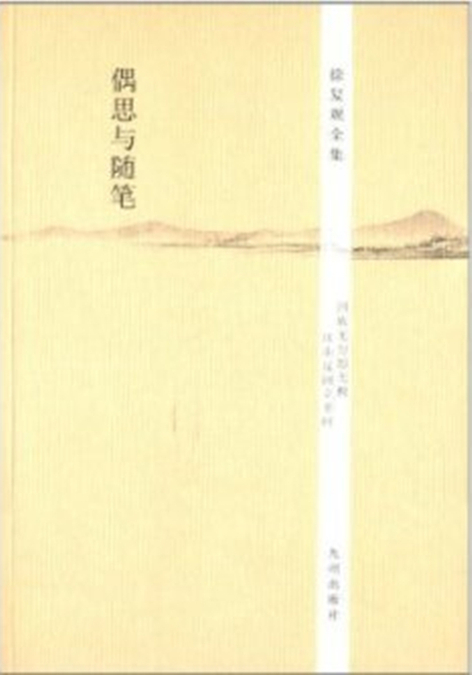
1975年,唐君毅出版了《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感念于“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而大声疾呼华夏族民应“灵根自植”,亟亟以求发扬中华文明之辉光于世界。不独唐君毅如此认识,钱穆、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当代新儒家皆悲悼于20世纪中国政治的波澜迭起,中国文化恰如浮漾其中的孤帆扁舟,载沉载浮,行止之间每困窘于现实政治的摧折。而正因遭逢史此一困局与变局,上述诸人才更坚信文化有淑世拯乱、贞定人心的重要作用。由此他们既讲学上庠,希冀以对中国文化精神作出全新的开显来因应世道,改变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否定的态度。
就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来说,钱穆的博通闳识,唐君毅的思理清明,牟宗三的朗妙通达,方东美的幽玄清雅,皆令我叹佩心折,而就中徐复观的峻厉与萧逸则更惬我心。
徐氏著作中荦荦大者,如《两汉思想史》、《中国人性论史》、《中国文学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艺术精神》等,体大思精,或纵论两汉时期社会结构与专制思想、或论述中国文化中对人的生命的根源、道德的根源的基本看法、或抉发中国文学之精神、或阐扬中国艺术的文化根性,胜义纷呈,至为精彩。在这些大著之外,徐氏亦有《学术与政治之间》、《论智识分子》、《偶思与随笔》等随笔集,针砭时弊,评骘人物,每能于现实的注思中发见恒常的思虑。
徐复观早年歆服鲁迅,于鲁迅杂文笔法特有会心。加以其性格的峻刻,从政的阅历,观世论事,较之寻常学者,每多一份老辣峻厉。而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文化的现实境遇特持痛心之论:如其直言“懒惰才是妨碍中国科学化的最大原因”,指出“当一个民族堕落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弱点,总不肯从自己的根源上去找原因,总不肯从自己的根源上挺身站起,而一定把原因投射到外面去,在外面找一个替死鬼来为自己负责”;嘲讽那些“常常把外人著作,随便找出其中容易歪曲的几句话,以‘介绍’为名,大发高论”者为“文化买办”,痛切呼吁中国要多一些“文化的民族资本家”,“把西方的文化、源源本本地介绍进来,以增加中华民族精神的营养”;率直道出在二千年专制历史的压迫下,“士农工商的四民中,以‘士’的人格最为破产;在历史中,由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坏的作用,绝对大于好的作用”。而其对社会世相的沉沦日下亦不避时讳,针对国人纷纷以学外语、讲外语为荣,他呼吁应使同胞有一种“精神属籍”的光荣;批评为官者“只顾自己乱扯”,根本不会做事,而这现象充分见出“因为大家没有人格尊严的观念,根本不感到这类的乱扯,是有伤他人的人格尊严”;痛责台湾“文化上的官商勾结,较经济中的官商勾结,将更为丑恶”,而“文化上的保护政策,乃是愚蠢残酷的结晶”。凡此种种,皆可见出徐复观对社会衰弊之相的不容假借,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在其中的毫不作为甚且多有助力极表不满,可称下笔如刀。
不过徐氏文章之峻厉,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写作态度上的严苛抑或知识分子对于纷纶世相的不满。事实上,徐复观从一开始就抱定不写不食人间烟火之文的宗旨。他自认“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作家”,而硝烟行伍、宦海风波又使其饱经巨变,更自陈要认真考量创痛巨深的世变的前因后果以及前途归结。杂文、时评与随笔,虽感触时事,缘机而发,究其实,却正是徐氏对于时代巨变所思所虑的一种透显,是其由批评世相而开展文化思考的一种凭借,不容小觑。此外,徐复观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序言中亦郑重强调,“凡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通过时代的具体问题,以呼唤时代的良心、理性的时论文章”,即“都是圣贤志业之所存,亦即国家命运之所系”。进而,他更指认一个政治清明的强盛国家,必有真正的舆论来作社会对于政治的指导,而“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换言之,时代的巨变,人世的乱离不容他涂抹风月文章、高文典册,政治的淆乱、权力的压制不容他作苟且的颂词、违心的逢迎,峻厉风发的背后是深沉悲愤的历史质感,是对于时代趋归的方向以及文化的价值与地位的忧思彷徨。
但若仅以怵惕惊心、中有汤火来评价徐复观文章,亦或许忽略了其文峻厉中有萧逸、悲愤中寓闲雅的特点。峻厉固然每老辣透辟,若止于峻厉,则不免有伤刻露,少了些摇曳生姿。据徐复观学生杨牧所述,徐氏于韩愈文章沉潜颇深。韩文的气盛言宜,徐复观显然别有领会。虽则其杂文在以国家时代兴亡为念,却每能于浅平琐细处叙起,娓娓道来,尤以《偶思与随笔》中大量谈论香港之文字为代表。徐氏客居香港期间,对香港之现状与未来多有关切,尤其是中国文化在时为殖民地的香港的存续状况,最是措意。但之于这一议题,徐复观并未写堂皇大文,相反采鲁迅笔法,多择取港地见闻以为点染。或自戏剧《杨门女将》牵连谈及传统在现代的接受与再创造,或自香港的高地价论及执政者对香港未来前途所应具备的基本态度,或从“黄色文化”来强调小市民卫护自身精神的重要性,所论无一不切近日常人事,对香港现状与未来的分析读来特别入情入理。
而所谓萧逸,亦不仅说徐氏杂文贴近凡俗生活,无谈玄之气,要知此种萧逸实乃一种基于文化理想而获致的挺特超拔。亦即其自述对于中国文化在解决中国今后问题中所占的地位的问题,有“一个确然不可移易的分际和信心”。换言之,就事论事与就世论世,皆非最根本的旨趣所在。相反,对世相的批评,最终仍旧是为彰显中国文化完全可用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坚信,使其即便议论当下,也不致陷入现实的泥沼,反为现实所吞噬。
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充满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忠恕精神,“却不曾发现实现此一精神的生活方式”,所以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民主形式”。且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并非形单影只,相反政治“在形式上很重,在精神上却很轻”。以此观念来看徐复观的杂文写作,未尝不可说杂文恰是其用为实现中国文化忠恕精神的一种具体方式。通过对当下现实最直截的观察,最严厉的批评,同时以传统文化的博大莹润来激起现代人的生命感应与人心照面,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在峻厉与萧逸之间,徐复观杂文与其学术著作一般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而其中所论,即便置于今日,或亦足资参考。
文 / 顾文豪 自由撰稿人,上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64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649号